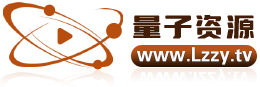FIRST青年电影展评委会大奖《燃比娃》导演李文愉专访 -
2025年盛夏,高原的西宁之夜,李文愉导演的电影《燃比娃》荣获第十九届FIRST青年电影展评委会大奖。影片以二维手绘的水墨系统为介质,重述少数民族的古老传说,也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呈现中国动画的可能性,用陌生化的长片语言解构人和传说的成长与进化。

当我们站在此刻梳理《燃比娃》这部二维手绘动画电影一路走来的萌生和壮大,用坐标轴上一颗颗明确的锚点更为直观——2021年开发初期,李文愉几乎是带着手稿入选FIRST青年影展年度电影计划并获奖,这也与今年夏天《燃比娃》在FIRST的入围和获奖冥冥呼应,正如李文愉所说,“我们本身就是创投出来的,再到西宁,这是一种具有纪念意义的回归。”2024年6月,《燃比娃》入围法国昂西国际动画节WIP单元并举行全球路演;2025年2月,《燃比娃》全球首映,入围第75届柏林电影节新生代 Kplus竞赛单元;6月,上海电影节期间,《燃比娃》作为“SIFF动画”单元的第一批片单影片亮相,并进入电影节开票榜单TOP20。
值得一提的是,《燃比娃》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限公司出品。上美影自1982年《三个和尚》和1984年《鹬蚌相争》入围柏林,时隔四十年才等来《燃比娃》照亮荧幕的火光。

《燃比娃》海报
在技术革新、手法多元的当下,《燃比娃》这样朴素的手绘长片无疑是个特例。影片采用水墨画为核心视觉语言,融入沙画、定格动画、剪纸及羌绣等多元技法,通过双线叙事结构展现远古先民生活图景:讲述猴形少年燃比娃追寻母亲阿勿巴吉的足迹,战胜恶煞神喝都夺取火种,最终褪毛成人的故事。这是燃比娃的成长之路,同时也承载着李文愉的成长印刻。
整部动画几乎都是李文愉亲手绘制、渲染完成,那些堆积的手稿体量庞大,质朴而坦诚地成为工作室里的珍贵留存,也成为这位气质淡漠的青年导演身上少年心性的一点佐证。“我一直都想独立完成一部长片,之前在动画节看过国外有独立制作的案例,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做一部长片也不是不可能。”李文愉说,“除了独立完成,我也希望保留一些‘粗糙’的质感,包括比较自我的部分可以在影片里呈现。片子里有一些铅笔线稿没擦,就是因为我想保留一部分创作的痕迹,还有这个‘成长’的大主题,也有我本人的心理投射在里面。”

《燃比娃》手稿
制作《燃比娃》之前,李文愉凭借《GotoCityELE》在第31届华沙电影节摘得最佳动画短片奖项,《oh&yeah》《公交车》入围昂西动画节等数十个电影节。更早之前,他的介绍里还是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的“老师”身份,导演和大学老师的头衔互相交缠,直到他独立完成动画长片《燃比娃》,用动画语言的独特性和广泛的可能性探索了长片的叙事边界,也完成自我意义上的锻炼和成长。《燃比娃》的片尾字幕里,很多职位都填着李文愉的名字,“我的创作习惯还是比较个人化,尽管辛苦,但能随时取舍,走不通就换。”

导演李文愉
7月28日,青海西宁,《燃比娃》获得第十九届FIRST青年电影展评委会大奖。推荐语这样写道:以二维手绘为介质,重述少数民族传说。其水墨视觉系统尤为卓异:流动的墨迹在严寒中构建出既原始又诗性的神秘场域。这不仅是风格的抉择,更是对动画本体语言的凝神回归。创作者以帧帧劳作,使古老神话在冷冽的影像肌理中获得当代再生。
在这个厚重绵久的神话包裹下,内核是“成长”,也是李文愉自始至终想要表达的主题。原始蛮荒的环境里,风雪凛冽,主人公前进的每一步都要克服诸多困难,身心双重进化。“我一直都想做一部关于成长的影片,当时看到燃比娃盗火的传说,我觉得成长和进化的概念是相似的,先民进化,普通人成长,可以互为隐喻。”去阿坝州采风、收集了大量资料后,李文愉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比起口耳相传的传说,羌族的建筑和风土人情在影片里体现更多。而燃比娃盗火,盗火和进化更像是成长的过程,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把传说和普通人的成长故事结合,融入一些符号性的东西,本质还是一个人的成长,如何突破内心。”

《燃比娃》剧照
交谈中,李文愉着重提到“恐惧”,无论影片里燃比娃面对怪兽的恐惧,还是现实他本人面对上台发言的恐惧,包括更早之前,他独自去到陌生的城市工作而产生的孤单和恐惧。这些真实存在的情绪都成为导演创作的具象呈现,“电影里的那只怪兽就是恐惧的具象化,但实际上它是假的,根本不存在。燃比娃一开始不断逃避,到最后真正面对,结果发现恐惧是虚无的,但不管有没有击败这只怪兽,这个过程里他都完成了自己的成长。我在影片里定义的成长就是敢于直面内心的恐惧,就像我上台发言也会恐惧,但认真去面对了,也是成长。”
李文愉生于1982年,既是导演、编剧,也是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数字艺术系副教授。他整个人的气质儒雅淡漠,表达也是平淡的,没有明显的语气波动。这样一个“淡人”,却坦荡表示:自己不介意在影片里投射个人情绪,无论对内制作还是对外观赏,他都更想看到导演内心独立并试图表达的内容。他也在平静的叙述里剖白,“其实整个影片就是投射了一段我自己的故事,毕业来到陌生的城市,很孤单,有时也很恐惧。当时我养了一条狗,它陪了我十二年。影片里陪伴燃比娃的狗狗胸前有块红色伤疤,其实就是我家狗胸前肿瘤的对照。”

《燃比娃》剧照
电影里的两组进化对照,燃比娃从猴子进化成人,“狗狗”从狼变成犬。而电影之外,李文愉在担负大学教职的同时,以一己之力承担着影片编剧、手稿的绘制和整体制作,这个关于成长的故事,最终也成为他本人人生阶段的鲜明注脚。“我们不停地面对恐惧,也以不同的方式战胜恐惧,这个结果本身其实没有那种重要,因为在过程里,我已经抵达了自己试图拥有的平静。”

INTERVIEW
Q:这是你的第一部动画长片,可以看到片尾字幕工作人员几乎都是“李文愉”。独立完成一部长片的愿望实现了,现在回想,过程里有没有什么特别困难的时刻?
A:最大的困难是我第一次做长片,整个制片流程比较难把控。以前做的都是短片,最多十来分钟,节奏进度的把控没有那么难,但长片是完全不同的体量。而且我的创作习惯比较个人化,基本是独立制作,或者组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小团队,有朋友和学生参与进来。因为人少,整个工程量就是很大的困难,但反过来想想,有利有弊,由我主导的情况下有些东西就可以取舍,某种效果达不到我们就干脆换条路。
Q:制作《燃比娃》期间,你的大学教职是如何兼顾的呢?
A:我负责的课程不是一个学期从头上到尾的,比如这门课集中授课三四周,那段时间里我的动画就稍微放放,专心上课,晚上回去再接着做。其他不用上课的时候,我基本就是白天画画,晚上在电脑上做一些合成工作。那段时间确实是累,夜里两三点睡是很常有的事。做完之后,我感觉自己衰老得特别快(笑)也是因为没有独立做长片的经验,自己在时间规划上没安排好,加上制片那边也挺急的,时间比较赶,我就一直在做。
Q:你提过,自己非常沉迷动画语言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A:当时我们做《燃比娃》,包括上美影和我们合作,是因为市面上主流动画电影的制作更偏向于电影语言,类似于好莱坞的电影语言。但我们做短片就会尝试动画语言的各种可能性,用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材料、图形,还有动画的变形等。这些东西我也在制作时放进了《燃比娃》,其实整部影片的叙事性是比较靠后的,我更多还是想在视听层面给观众一些新鲜感。我觉得能在长片里“玩”一下也挺好的(笑),但后期发现如果太实验的话,观众可能不太容易捕捉到一些信息,所以我们还是稍微收了收,加了旁白,更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Q:影片里贯穿着“火种”的追求,你也说过,收集资料的过程里发现世界上每个民族和地区都有类似盗火的故事。你是怎么理解先民对盗火的追求?
A:我觉得学会使用火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开始,感受火带来的温暖,吃熟食,人类才开始进一步进化。人类发展的过程里,就是逐渐学会使用不同的工具,火、蒸汽、电力、新能源,这些是进步的标志。所以我把对火的追求放在影片里,作为一个符号性的东西去象征进化。
Q:前期准备阶段,你在阿坝州采风,收集了大量资料,但《燃比娃》没有被限制在原本的传说里,反而有一些相对现代的表达,比如爱与陪伴,人和动物之间的那些特殊联结,你是置放了一些和自己宠物的感情进去吗?
A:其实整个影片就是投射了一段我自己的故事,我刚毕业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很孤单,有时也很害怕。当时我养了一条狗,它陪了我十二年,后来因为胸部肿瘤去世的。在陌生的城市里,狗狗陪伴我走过了很多日子,对我来说这是人生的一段路程,却是狗狗一生的陪伴。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表达。狗狗陪伴人类,人类不停地面对恐惧,完成自身的成长。
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成长,不是完成了某件事,而是在完成这件事的过程里,学会了面对一些东西。比如燃比娃敢于面对恐惧,我其实上台发言还是比较紧张的,我也面对了这种情绪,这些都是成长。
Q:从最初选择这个行业的心态出发,你现在做动画最大的快乐和成就感源于哪些时刻?
A:一开始我是学画画的,又很喜欢画漫画。随着逐渐深入接触动画,我觉得很多时候快乐都源于创作的不确定性,比如一个画面做出来,其实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是全新的感觉了,这种时刻就很快乐。又比如,我在脑海里想要一个效果,其实不知道最终会是什么样子,等到真正做出来,看到那个成品,心里也会很快乐。这些画面不断累积的快乐,直到完成一部作品,就会更快乐。做动画的过程在外人看来很枯燥,我承认确实也有枯燥,但每个动画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去把这些枯燥转化为快乐。我身边做动画的同行们看起来都挺年轻,不太有年岁痕迹,可能因为每天都在创造一些新东西,不断动脑筋,观察力也很敏锐,心态更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