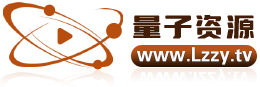《生万物》:当土地叙事有一场“女性史诗” -
国产剧中长期的女性视角转变趋势,正在进入到乡土题材之中。
最近播出的剧集《生万物》改编自赵德发“农民三部曲”《缱绻与决绝》,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鲁南天牛庙村宁、封、费三家两代人跨越数十年的命运。作为央视年度剧集,它从开播开始讨论度就居高不下,更以8月收视冠军收官。
串联起这宏大史诗的,不仅是村里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更是无法让人忽视的女性角色的命运钩沉,和来自女编剧对角色结局的改编,完成了一次从男性史诗向女性叙事的体系性迁移。
这让《生万物》有了女性对于传统礼俗的突破与反抗,有了她们主动踏入“父权制”土地的决绝。即使仍有悲剧和不甘,这依然是一场土地叙事回归女性本位的大胆尝试。

剧照 图源:豆瓣 01 从“土地祭品”到变革者
最原始的土地崇拜便是母性的,上古时期的“后土”之称是原始母系社会在土地崇拜中对土地的女性化神赋,古希腊神话中的农业女神德墨忒尔,也是大地、母亲、丰产的联结。万物之母,是循环与生命的源头,其神格形象天然与孕育、滋养、循环等女性特质相连。
《生万物》正片第一幕,是杨幂饰演的宁绣绣踏着土地抚摸石牛开始七十年前的回忆,女性与土地的关系在剧中成为启幕的篇章。宁绣绣如果不出意外,原本会像传统礼俗所安排的一样,作为地主千金嫁入门当户对的人家、安心成为妻子与母亲。但是在出嫁当日,她被土匪掳走,父亲宁学祥却以土地是家族根基而不愿卖地赎人,作为身份与地位象征的土地,与女性的生存处境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当宁绣绣从土匪窝子逃出,以决绝的态度离开宁家下嫁封大脚,公公讨要十五亩土地作为陪嫁,再次印证女性只不过是具有物质生产价值的土地的陪衬。
成为陪衬或者“土地祭品”,并不是乡土中国里一个女性个体的命运。蓝盈莹饰演的银子,放弃与佃农儿子铁头青梅竹马的感情,为了能养活自己家人的“十斤地瓜干”,选择嫁给年迈的宁学祥。
以宁绣绣为代表的女性形象,在以土地强化性别权力结构的传统社会中,试图去聆听土地与人真正的关系,而不是被权力、利益的争夺蒙蔽了双眼。宁绣绣嫁给封大脚之后,学习锄地挑粪,又带领村里的妇女识字、种田,收获了来自自己汗水的第一袋粮食,这象征着女性通过劳动重新与土地缔结盟约,恢复其本应拥有的、与地母相连的主体身份。
当宁绣绣决定为救济灾民不运走粮食,宁学祥开始去恳求宁绣绣,银子为了封家帮宁家忙割麦不白帮忙,命令宁学祥去发该付的金额,主导土地的角色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剧中的女性不再仅是土地史诗的注脚,而成为主动走入父权结构、与之对话甚至抗衡的行动主体,完成了从“父的土地”到“母的土地”的语义转换。尽管剧中女性仍需面对历史洪流的冲击,但她们已迈出从“祭品”变革者的关键一步。
02 土地与女性的诗性共语
《生万物》名字,来源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家哲学。土地见证着万物化生、世代循环,《生万物》用绵延不绝的实景麦田、日日不息的劳作景观、暴雨中的匍匐护秧、芒种开镰的仪式,甚至是宁绣绣捧起的一抔黄土的颗粒中,构建属于乡土风沙中的诗性。像宁家悬挂着“土生万物由来远,地载群伦自古尊”的祖训那样,土地是天牛庙村人们的精神承载,也是中国人的原乡。

“你不能不敬你的爹娘,也不能不敬你的地。你要是对它亲,对它诚,它用收成,来报答你。”这是林永健饰演的农民封二在秋分前一天,对家族子弟的告诫,他意识到自己即将离世,人们对他的印象是碎嘴算计的市侩模样,但提及土地,他依然是饱含热泪,这也是他临终前最后的宁静的嘱托。从土地生,从土地死,他是这片天地对土地与庄稼眷恋的人们的缩影,也是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说的那样,“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数代人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根,熟稔,续写着年复一年的生活。
导演刘家成曾表示,“《生万物》写的是农耕文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这是宏大的主题,但它的叙述方式却是家长里短,生活气息浓厚。”《生万物》所引起的剧烈反响,“俺爹”“俺娘”等乡土气的称呼,都离不开中国人对于乡土的浓重情怀,对土地深沉的热爱造就了剧中这份诗意。
与许多年代剧不同的是,这次关于“地”的一字诗,有很大部分来自剧中的女性角色。
相比于原著《缱绻与决绝》,剧版编剧王贺对其中有着悲惨下场的女性角色都有了大刀阔斧的改编,打破了观众对乡土叙事中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除了对女主角宁绣绣的悲惨结局的改写,赋予她自我拯救的能量外,村里嚼舌根的不再是“长舌妇”,而是田间地头的男性,大脚娘也不是传统剧集中毫无情面的恶婆婆,而是体贴改嫁来的宁绣绣,在清贫的日子中仍然温柔善良。
即使对那个时代的书写,仍不可避免地迎来许多女性被所谓的家族遗训、旧有礼俗所带来的悲惨结局,但是女性与女性之间的温柔、女性对土地真切的关照,都为这部剧的诗性添加了母性、温暖的光环。《生万物》让女性叙事重返土地,实现土地、女性、母性的神性三者的符号耦合,也告诉观众,土地不仅是父权的、家族的、政治的,也可以是女性的、身体的、诗学的。
03 当“土地叙事”进入女性视角
文学作品与影视剧中的土地叙事,包含描述农耕劳作的行动、乡土情结、民俗风情与发生在土地之上的情感故事。然而在漫长的叙事史上,土地逐渐被父权话语所征用和重构。这关联着从母系氏族到父系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农业技术发展,男性在体力劳动和部落组织中的作用凸显,土地的经济价值压倒了象征价值,土地被纳入父权继承体系。中国传统乡土叙事也相应地长期被男性视角主导,女性则被排除在土地叙事权之外,沦为土地上的沉默者、交换物或牺牲品。
莱斯莉·克恩在《女性主义城市》中这样表述:“我们的城市是用石头、砖块、玻璃和混凝土书写的父权制。”农村的土地亦然,它象征着基业、家族根脉,甚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权力。对土地的影像书写同样不离开男性本位,男性作为“劳动者”的典型视觉形象,不需过多铺垫,便能直接引起观众对土地的情感。
21世纪早期的国产剧中,大部分延续了这种叙事。《白鹿原》的故事主线,围绕白嘉轩与鹿子霖展开,女人不过是糊窗户的破纸。《闯关东》中,山东人朱开山一家去往东北开荒,求生谋存的主力仍是身为一家之主的男人。《平凡的世界》从孙少安和孙少平的视角出发,去描述劳动者与奋斗者的精神,而其中的女性,则无一不是坚韧质朴、隐忍奉献的角色。在男性角色背后,是被几乎不可动摇的贞节牌坊困住的一代代女性。

图源:豆瓣
国产剧在最近十年开始了剧烈的女性视角转换,但在年代乡土剧中,男性本位仍然十分坚固。不过在这几年,诸多土地叙事文本开始加入女性视角。在年代剧《六姊妹》中,女性的形象没有被简化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贤妻良母,而是让六位姐妹对于传统规训,做出了或叛逆,或勇敢,或大胆出走的行动,在淮南旧城的土地上,主动参与到充满希望的建设之中。《幸福到万家》中,何幸福为土地补偿款而抗争,为水质污染而起诉企业,土地权益成为女性维护自身及社群权利的切入口。当女性和土地拥抱时,权力、阶级、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似乎都走向了末置,她们与土地回归了纯粹的共鸣,土地回到了让万物生长的滋养者本位,折射出土地超越经济价值的伦理与情感意义。
《生万物》虽在女性叙事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重构的不彻底性也十分明显。在关键情节推进与重大决策场合中,叙事权仍惯性般地回归至男性角色手中。土地交易、农会议事、家族规训等公共场域,女性依然处于失语或陪衬状态。这种叙事断裂很大程度上源于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20世纪上半叶,父权制仍牢牢掌控着经济与伦理权力,塑造女性角色的同时,也必须尊重时代背景的客观逻辑。
《生万物》并非完美,但无疑为乡土题材剧作提供了新的叙事路径。当在带着近乎神圣的仪式感、滋养万千家庭的土地叙事加入女性视角时,不仅要在叙事上超越苦难陈列与道德同情的传统模式,重构女性与土地的关系,让女性角色更丰满、立体、具有主体性,也要关注那些在土地上发生的女性主导的“不被书写的日常”,如劳动技术的传承、民间信仰中的女性神明等。“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在劳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女性,仍要不断在土地叙事中去争夺主体权,或许《生万物》这样的范式革新将继续发生。